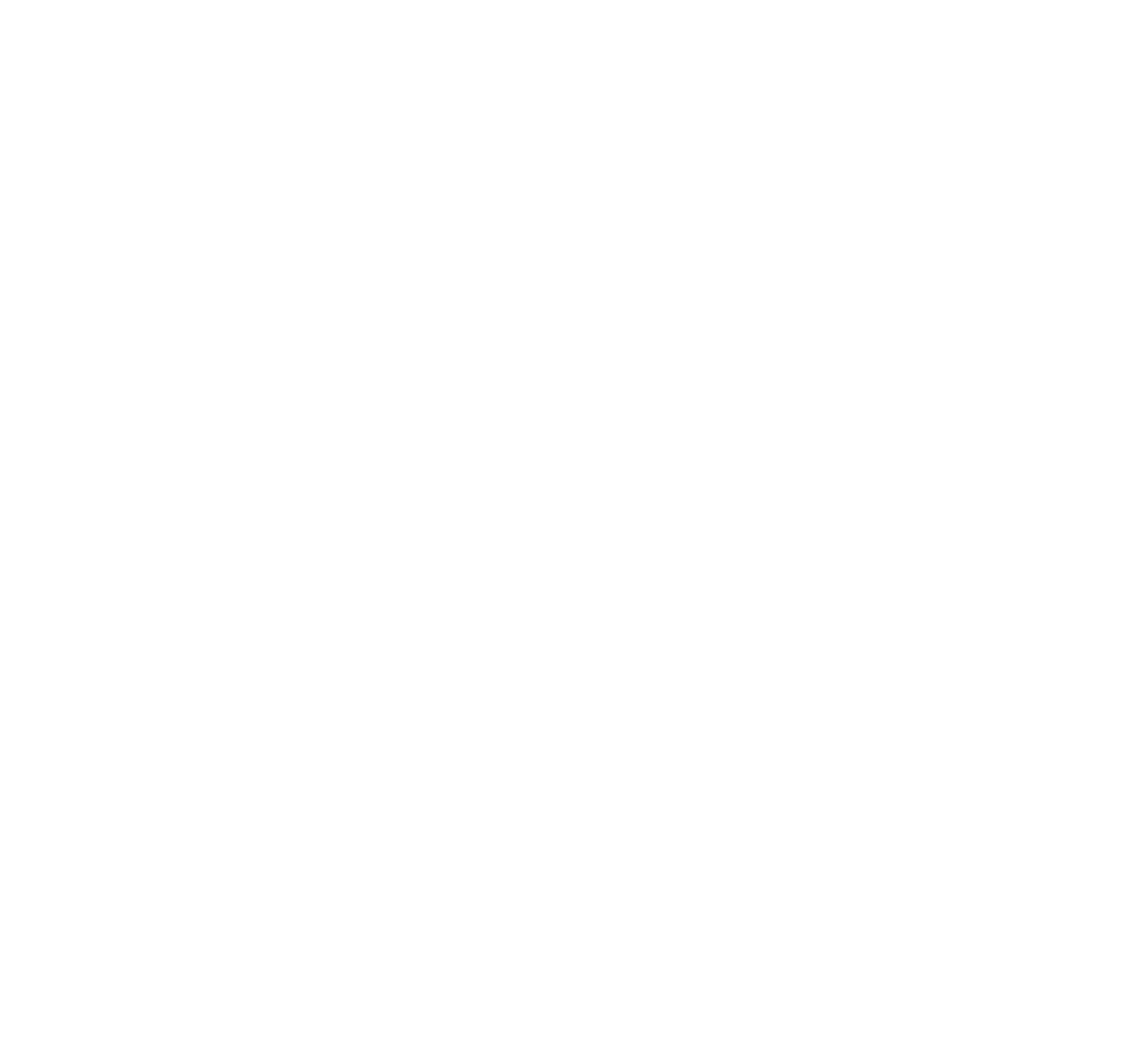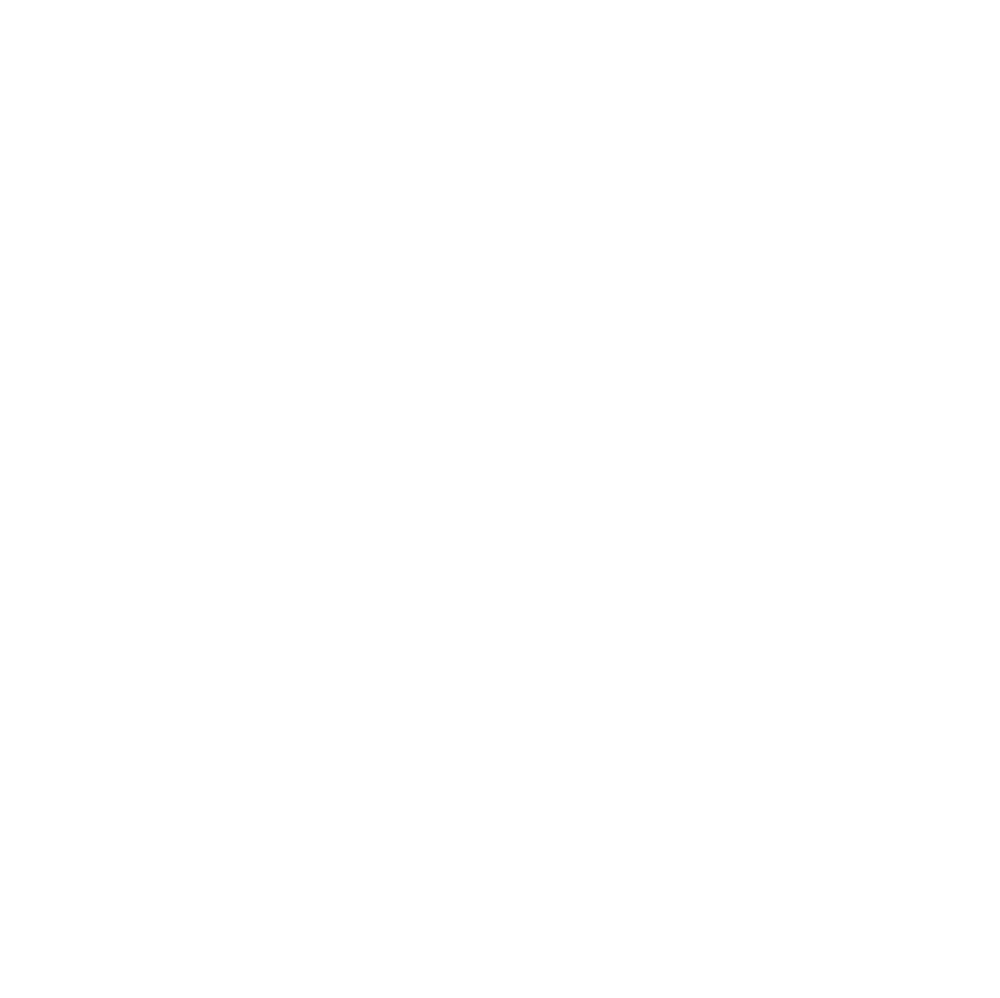![[pdf图标]](https://www.iucr.org/__data/assets/image/0020/12359/pdficon_large.gif) 威廉·托马斯·阿斯伯里
威廉·托马斯·阿斯伯里
1898-1961
W·T·阿斯伯里是威廉·布拉格爵士最早、最忠诚的门徒之一。1898年2月25日,他出生于英国陶器区斯托克顿的朗顿,出身卑微,这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事实。1908年至1916年,他在朗顿高中接受了中学教育。奖学金使他能够去剑桥学习化学。1916/17年和1919/21年,他在那里,参战。在自然科学三人行的两部分中,他都获得了一等成绩,1920年的化学、物理和矿物学,1921年的物理。1923年,他搬到伦敦大学学院,在W.H.布拉格教授的带领下,他立即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演示者,布拉格教授将他带到皇家研究所和戴维·法拉第实验室担任助理。阿斯伯里在皇家理工学院工作了五年,是威廉爵士聚集在那里的一群热情的年轻工人的灵魂和催化剂(参看第七部分中的J.D.Bernal和K.Lonsdale)。原因在于他对晶体结构分析这门新学科的无限热情,他喜怒无常的态度,以及他谈话中出乎意料的、有时是挑衅性的、但往往是最有帮助的转折。
1928年,阿斯伯里在威廉爵士的推荐下来到利兹大学,该校将开始羊毛物理和化学的基础研究。1928年,他成为纺织物理讲师,1937年成为读者,1945年成为新成立的生物分子结构系和实验室的教授。从职业生涯一开始,阿斯伯里就强调羊毛和其他纤维的化学和物理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它们的X射线衍射效应,这些物质无法提供与单晶相同精度和丰富程度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将所有可能从它们的物理和化学行为中收集到的证据结合起来,这一讨论往往需要极大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阿斯伯里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帮助他走上了更焦虑的科学家们可能不敢涉足的道路。Astbury部门的指定是同类部门中的第一个,Astbuy为这个名称感到骄傲:生物分子结构;此后,英国和外国的其他大学的系或实验室都采用了这种名称。正如Astbury设想的那样,这将是一个可以利用化学、物理和生物特性,结合显微镜、电子显微镜、X射线和电子衍射以及其他看起来有希望的东西,以一种捉摸不定的方式攻击分子尺度上的生物结构和纹理的地方。1959年,当我最后一次在利兹见到阿斯伯里时,我在每天的实验室茶会上发现了他,他主持了大约八位同事,他们都是非常成熟的科学素养,并像以往一样领导着富有挑战性和生动的讨论。
根据Astbury自己的评价,他最重要的科学贡献是关于头发、羊毛和相关纤维的结构的三篇论文(事务处理。和程序。罗伊。Soc公司。,A 1931-35),他对蛋白质变性的研究(1935年;他曾提到的水煮鸡蛋),以及他的细菌鞭毛衍射研究(1949年,1955年)。他写了一本书纤维结构基础(牛津大学出版社,1933年),在给德阿尔西·温特沃斯·汤普森的演讲卷中发表了一篇关于“生物分子的形式”的值得注意的文章关于成长和形式的论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45年),并于1945年在皇家学会发表了克罗尼亚讲座“生物纤维结构与肌肉问题”。此外,他还是物理、化学、生物、纺织技术和普通期刊上论文的多产作者,也是一位伟大的讲师。他杰出的作品获得认可,记录在他获得的奖牌、奖项、荣誉学位和会员资格的长长列表中。
阿斯伯里与凯萨琳·朗斯代尔爵士一起为这本书撰写了关于英国早期X射线衍射的文章,尤其是在皇家学会。他开始写作,在他的论文中发现了一个草稿页,这是他很有特色的,尽管当时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种病已经使他丧失了能力,没有什么能比把它添加到这份通知中更好地描述他活泼的个性了。这将比许多文字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阿斯特伯里是早期晶体学家中最受欢迎的人之一。
P.P.埃瓦尔德
早期在伦敦大学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戴维·法拉第实验室工作
在分享谁应该在这些X射线衍射回忆录中写什么时,可以回忆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皇家理工学院早期时光的两位“老手”显然是凯瑟琳·朗斯代尔和我,但尚不清楚的是谁应该写实际的东西。有时只有我们中的一个人记得,我们很难说“我们记得”,总之,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有独特的风格;所以我们妥协了——我是说,她同意让我做这件事。但应该理解的是,这是一项共同努力,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任何特定的记忆或轶事都可能是其中之一或两者共同的。在本文中,我们将被视为一个整体,就像《缆车手》中的两个未解决的继承人一样。
就年龄和结晶学而言,我是这两个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因为我在服役两年后,于1921年加入了大学学院物理系,而凯萨琳(当时是亚德利)在毕业后比大多数人年轻两年,于1922年加入了该系。除了物理,我还在剑桥大学读过化学和(古典)晶体学,1922年我也结婚了,所以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人冒险带着这个早熟的孩子,至少有一个简短的开始。这是一个盲人领导盲人的好例子(稍微混合一下比喻),但这当然是件有趣的事。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最大资产是它的幼稚,我们一定是这方面的杰出例子——我们所有人,甚至不排除威廉爵士的高水平。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请允许我明确指出,威廉爵士——我们在背后称之为老人或比尔·布拉格——从技术上讲从未“领导”过我们任何人。这不是他的方式——如果他有办法的话——如果你够蠢的话,你甚至可能会声称你“领导”了他,因为,特别是在1923年我们移居到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法拉第实验室之后,当他突然出现在你的房间里时(不是很频繁),通常是问你一个与他即将发表的演讲有关的问题。或者你可能会在楼梯上遇到他,他会说:“你好!家人好吗。他尽可能经常来喝茶,在那里我们很少谈论“商店”。
![[pdf图标]](https://www.iucr.org/__data/assets/image/0020/12359/pdficon_large.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