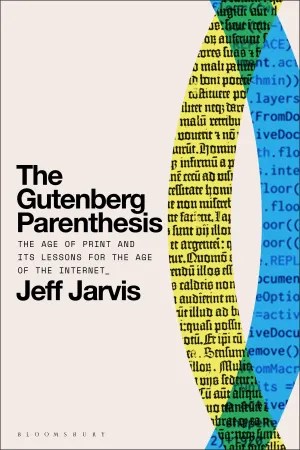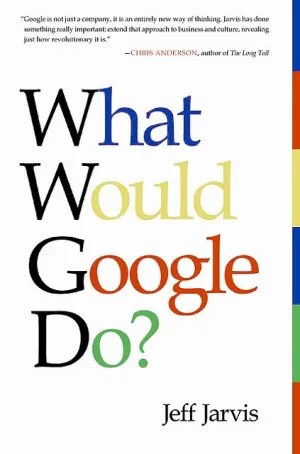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一直在避免从事互联网和新闻工作:也许是时候放弃旧的新闻业及其传统产业了。
我说这话时,并不高兴,也不满足于试图让报纸和杂志改变现状,我对记者和其他在垂死的行业中工作的人以及那些依赖他们的人深表同情。 但旧新闻行业正急不可耐。 我不是建议对剩下的进行安乐死。 我也不在坟墓上跳舞。 在我经营创业新闻中心(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平衡对初创公司和传统公司的支持。 但我想知道是不是该停止把钱和精力花在不好的事情上了。
旧新闻业未能适应互联网及其每一位潜在的救世主 — 从平板电脑到付费墙,再到程序化广告,再到整合到十亿富翁 — 让他们失望了。 对冲基金买进了连锁店和票据,出售了所有没有固定下来的东西,削减了所有可能的成本,并将每一分钱的现金流带回家。 老公司仍在投资的一件事是游说。
在我在参议院的证词中 上周 ,我做了一件如果徒劳的话也是一厢情愿的事,敦促立法者不要制定 保护主义立法 与坐在我旁边的行业游说人士共同撰写,但目的是支持各地社区新闻业的紧急重建。 不太可能。
坏消息接连不断。 就在上个月 洛杉矶时报 是 解雇115人 ,将其新闻编辑室投入 “混乱”和“混乱” 时间 杂志 解雇 15%的工会编辑人员。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 编年史 亿万富翁为了挽救旧消息而损失财富的痛苦。 我认为对冲基金不可能再折磨新闻业,但奥尔登做了比买报纸更糟糕的事: 销售 巴尔的摩太阳报 对于小默多克来说,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是右翼辛克莱(Sinclair)主席,他憎恨新闻和报纸。 在英国 镜子 的发行量从500万下降到25万,当地报纸 溅射 公司预测 打印将不可持续 — 这是我20年来一直在警告的事情。 Once-grand(Once-grand) 体育画报 正在进行 谋杀 一目了然。 FCC只是 宣布 它正在努力支持当地电视新闻,尽管当地广播新闻的观众人数少、年龄大、正在死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是由观看人造福克斯、辛克莱的人组成的。
与此同时,人们对新闻业的信任度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 牛津路透社研究所告诉我们 三分之一的人积极回避新闻 谁能责怪他们? 我自己已经厌倦了旧新闻的一厢情愿的末日预言,它轻信地将政治报道为体育,它对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支持和正常化,它拒绝称种族主义为种族主义,它长期缺乏多样性,它对权力的依赖,它对技术的道德恐慌, 以及在复制和点击诱饵上浪费的资源。 Semafor和Gallup 报告 对记者的信任是 下落 现在也在民主党人中间。
现在出现了人工智能来制造和贬低我们称之为内容的东西,剥夺了旧新闻行业制造商品的价值感和目的。 我一直在试图说服新闻机构,他们不在或不应该从事内容业务,但新闻是建立在对话、社区和协作基础上的服务。 我失败了。
当然,也有例外。 波士顿环球报 和 《星际论坛报》 似乎还活着或更好。 我在Advance的老同事正在创新 阿拉巴马州 ,生活在 过去的打印 .(在他的 冗长的哀悼 在死亡新闻中,埃兹拉·克莱因将阿拉巴马州的绝版列为一种损失,当我说这是一场胜利:媒体死亡后的生命。) 《泰晤士报》 是 增长的 在游戏和食物的背面。 国家地方新闻信托基金会正在保存报纸 在这里 和 那里 .
但接下来是斯克兰顿,它的报纸现在被奥尔登抓住了。 《华盛顿邮报》 记录了他们的痛苦 2月9日,我将在斯克兰顿大学演讲 Schemel论坛 关于现在该做什么。 我应该告诉他们什么?
我会警告他们,不要削减开支,不要在他们亲爱的老人家进行投资或创新 时代论坛报 我已经看过奥尔登的工作方式。 十年前,作为Digital First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我看到该公司在John Paton和Jim Brady的领导下进行了创新,但当这并没有带来销售 2015年 他们两人都走了,海吉一家开始切骨髓。
我没有解决方案,没有拯救; 没有什么是这么简单的。 有很多人试图为新闻找到新的未来。 在我的参议院 证词 ,我谈到了 新泽西州新闻共享区 我很自豪十年前在蒙克莱尔州立大学帮助创办了这所大学; 以及475名成员 狮子 当地独立在线新闻出版商; 和425名成员 印度国家标准 非盈利新闻研究所。 另请参阅今天的新闻 19号正在启动一个新网络 分享新闻(几年前我在新泽西尝试过)。 这就是新闻创新发生的地方:自下而上,基层努力在社区涌现。
但作为我的老朋友和同事彼得·巴蒂亚 说 当他做出解雇新编辑的有争议的决定时 休斯顿登陆 “我们基本上是在网络上发布一份报纸。这并不是我们取得长期成功的秘诀,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秘诀。”我对休斯顿兰登不够了解,无法发表评论,但我确实担心,新新闻的一些努力仍在效仿和追求旧新闻的形式和功能。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激进,比我更激进。
我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新闻业及其在威权主义、反启蒙主义和法西斯接管威胁下的社会中的作用。 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 归属新闻 .和我的同事 凯莉·布朗 ,我帮助启动了一个学位项目 — 我们校友们开展的运动 — 参与式新闻。 还有其他运动寻求重塑新闻业: 解决方案新闻 , 合作新闻学 , 建设性新闻 , 报复性新闻 , 对话新闻 , 审议性新闻 , 团结新闻 创业新闻,以及 更多 他们分享的是一种首先倾听社区及其需求的道德,以及创新的紧迫性。
我乐观地注意到Mike Masnick刚刚发布的报告, 天空正在升起 关于互联网对媒体的影响 — 阅读、观看、聆听和玩耍。 它的结论是:“现在制作的创意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多的人能够创作内容,也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创作内容赚钱……而这几乎都要归功于互联网的力量。” 这份报告主要是关于娱乐业的,但也指出,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似乎互联网出版业的工作岗位取代了报纸和期刊失去的工作岗位。”
遗产之后可能会有生命。 记者将扮演一些角色。 但新闻学院必须拓宽视野,以教授更多内容。 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如何为众多公众服务?
至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告诉报纸编辑和出版商,他们必须想象有一天印刷业不再可持续,如果那时他们不能从数字上获利,他们就会死去。 现在,我要告诉斯克兰顿的好人们,想象他们的报纸有一天会死去,或者像死了一样好。
然后呢? 公民必须团结起来,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社区的需求:是的,需要信息,也需要理解、协作、责任、维修和服务。 他们需要决定什么对斯克兰顿及其众多社区最有利。
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些帮助,尽管永远不够。 按下“前进” 为这项工作带来了5亿美元,但这只能持续到目前为止。 新泽西公民信息 联合体 正在开展有趣的工作,为支持创新提供国家资金。 也许宾夕法尼亚州也可以这样做。 (尽管我担心在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或 奥克拉荷马 将支持。) 加利福尼亚 ,就像美国国会 JCPA公司 ,正在谈论帮助新闻 — 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代表传统新闻公司及其对冲基金所有者勒索科技公司。 JCPA明确排除了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新闻企业 — 也就是说,我上面列出的数百位创新者中的大多数人。 不用了,谢谢。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将是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并赋予他们权力,而不是在所谓的媒体素养方面,而是在媒体领导方面,为他们社区的健康和公众话语承担责任。 这是一个庞大、复杂、微妙、不确定的秩序,需要汇集远远超出新闻业的学科智慧: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区研究、伦理学、设计和艺术。
我不得不说,今天的报纸、电视和商业广播电台都不足以胜任这项任务。 他们的新闻是在大众传媒的漫长世纪中发明的,这一世纪始于(正如我在年所述 杂志 )当Frank Munsey意识到他可以以一分钱一分损失的价格出售同名期刊,但通过将观众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而获利时。 由此诞生了注意力经济,现在不仅腐蚀了旧媒体,也腐蚀了新媒体。 互联网并没有扼杀新闻。 它扼杀了大众,扼杀了媒体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神话:我们的注意力是一种可以拥有、购买和出售的商品。
我怀着不情愿和悲伤的心情说这话,但也怀着希望,因为我有幸看到我的一些校友尝试创建一种人类规模的新新闻,建立在倾听和服务社区的基础上,而不是怀旧。 斯克兰顿会怎么做? 这将取决于斯克兰顿,而不是无情的对冲基金 — 新闻纸的垃圾桶 — 这已经传到了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