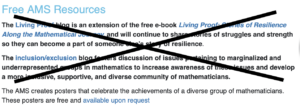由客人发帖公正数学集体
当我们达到2020年夏季黑人生活事件叛乱的一年标志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反思去年夏天我们承诺采取的行动以及在这一年中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我们在数学界的组织经验。Tl;医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像放牧猫这样经常感觉的事情也能如此快乐和鼓舞人心!我们在这里也要总结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竞选活动,让人们知道如何更多地参与我们争取更公正数学的斗争。
正义数学集体(JMC)成立于去年夏天,旨在努力推动我们的社区实现更自由、更公正的数学。一年后,在几次竞选活动启动后,我们以上述同样的反思精神撰写了这篇文章,并列举了我们的一些经验、胜利和挑战。
我们为彼此建立的联系、友谊和团结而欣喜若狂!我们的集体现在是50多名数学家和数学学者的组织之家,其中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终身教职员工;R1、教学机构和文理学院的终身教职和全职教员。坦率地说,我们很惊讶地发现这么多数学家对废奴主义数学的未来感兴趣!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沮丧。我们对那些继续袖手旁观的人的冷漠感到愤怒,这代表了我们自己和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利益。我们对那些在DEI行业但仍拒绝冒政治风险,将自己的名字贴在真正激进的想法上,或承诺采取可能会让他们与同事及其母国机构陷入麻烦的行动&因为现状阻碍了真正的正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总结我们一年的竞选活动,以及它教会我们的风险、资历和不同形式的权力,因为它们与数学界的组织有关。
“一旦我获得任期,我会说出真相”,以及我们对自己说的其他谎言
“现在摇摇欲坠太冒险了,你必须考虑你的职业和未来!等到你有了任期,你才有真正的力量做出改变。”JMC成员已经无数次听到过这条建议的版本,但大多数资深数学家对我们工作的投入都是对我们的竞选活动大加否定。鉴于承诺的行动和观察到的不行动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需要问:所有摇摆不定的终身数学家在哪里?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实现有意义和持久的变革所需的工作中,高级人员迄今为止发挥的作用最小。这种缺乏参与感是一种真正的耻辱,因为他们的工作保障使他们处于承担政治风险的最佳位置,并且因为他们的专业资历赋予他们在我们社区中的巨大影响力。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但我们想强调一下去年我们遇到的四种主要类型的高级数学家:
- 这个冷漠的学术
- 这个遭到军事反对
- 这个DEI专家
- 这个共犯
我们查看冷漠的学术以及DEI专家这是我们组织工作的最大障碍。
完全脱离接触有时比积极反对更糟糕。冷漠的学术不想以任何方式给人带来不便,原则性往往很不方便!当然遭到军事反对不是我们的朋友,但不像冷漠的学术他们至少诚实地承认自己有政治信仰(不管这些信仰有多么可恶!),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在公共论坛上表达这些信仰。
以及激烈反对分享坏的和/或错误的意见有时对我们的组织工作很有帮助。例如,考虑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中,有人宣布,他们非常反对道德观念,这一观念告诉学者们在哪里指导我们的劳动,如果撒旦雇用数学家,他们会亲自为撒旦招募。通过指出这一立场在道德上的破产程度,我们可以就学术自由与学术界道德参与之间的关系展开一场非常必要的对话。
与冷漠的学术,的DEI专家愿意给你带来不便。他们中的许多人花了无数时间组织针对代表性不足和边缘化学生的公平活动或会议。DEI专家他们经常把自己的工作描绘成完全不被注意和无偿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寻求“好麻烦”的叛逆学术活动家,右翼极端分子以他们的努力为目标就是明证。这种说法的一个问题是,右翼极端分子不会从地下的一个洞里知道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此外,真正的“好麻烦”实际上需要有陷入麻烦的可能性!由于DEI专家他的工作得到了制度上的认可,他们很少需要担心这一点。
沿着这些思路,联合军委会认为,传统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DEI)很有效,就像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样,根本无法解决我们社区不公正的根源。无牙的DEI工作为我们的机构提供了掩护,使他们能够清洗自己的声誉和假装关切,而不会对他们受益的压迫性制度进行有意义的彻底改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的DEI工作实际上充斥着大量的资源和机构时间,领导这些工作的人往往会得到个人的赞誉、晋升和社会影响力的认可。
最后,也是最不幸的一点(在数量上!),我们有共犯一些人已成为联合军委会成员,并为我们的积极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坦白地说,正是由于他们,我们集体中越来越多的初级成员知道,终身制和诚信并非不可能!
经验教训:我们绝对不能依赖高层人士。该体系对那些愿意维持现状的人给予了太过压倒性的奖励,而不是对拥有激进政治的资深人士的强大队伍的存在。作为个人,我们不会放弃他们,但我们不能等待他们。
权力:谁拥有它,谁没有?
显然,拥有终身教职的高级数学家做拥有权力和安全,但我们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的界线在哪里?没有明确的方法来衡量权力,这使得如此多的高级学者,包括主席,在被要求实施甚至是最微小的部门改革时,都有可能声称自己无能为力。不同的人可以获得不同的权力,但任何人都可以感觉无能为力。没有什么环境比专业学术界更适合制造懦弱。研究人员受过训练,相信任何错误的举动都可能会在令人垂涎的终身职位和失业之间产生差异;也就是说,我们被训练来丧失我们的力量。这就是“等到你获得终身教职后再出海”建议的问题所在:到那时,这种训练已经完全内化了。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至少有一个权力底线:可以在付费墙后面导航的机构关系;有机会指导和教育学生,让他们自己在未来掌握权力;以及花时间在教室、办公室和走廊里,而今天活着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被禁止进入这些地方。因此,与其问“我有权力吗?”,我们认为更紧迫的问题是“我如何履行使用我的权力的责任做有吗?我如何不仅对我的学生和学员负责,而且对我在学术环境中很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人负责?”这些问题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但联合军委会的初级成员相信我们的力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发挥它来产生严重的影响。
当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终身职位,而且不同成员在权力和安全方面存在不可否认的差异。集体匿名是缓解这些差异的一个有用工具,集体行动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摆脱把个人视为关键来源的权力模式。集体行动是力量的源泉。当那些有权做出改变的人不愿意这样做时,要么是因为他们被投资于压迫性的现状,要么是由于他们太懦弱而不敢宣称自己的权力,或者更常见的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的目标是组织有足够能量、数量和动力的运动,迫使人们动手,改变文化。
经验教训:权力的观点认为,大多数权力归于老年人,而最少归于边缘化的人,这种观点是还原性的,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而不是集体。在某些方面,这种观点最终加强了我们想要废除的等级制度。例如,签署一项有风险或政治争议的竞选活动的人越多,该活动的影响力就越大,下一个人的参与门槛就越低。每次我们选择捍卫我们的原则时,我们都会行使和主张我们的权力,当人们聚在一起共同做到这一点时,就会产生新的权力。
监狱和警察之外的数学
大约一年前,公开信开始呼吁结束数学家和警察之间的合作。此时,JMC仍在组建过程中;一些JMC成员是合著者,许多即将成为成员的人在信写好后帮助编辑和宣传。作为废奴主义者,我们设想一个没有警察和监狱的未来,作为数学家,我们可以进入数学界。当人们相互了解并且有着预先存在的关系时,组织是最有效的,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影响范围内为我们的原则而战。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我们收集了数百个签名。回顾过去,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
- 人们对建立一个无政策的数学社区有着真正强烈的愿望。
- 在乔治·弗洛伊德、托尼·麦克戴德、艾哈迈德·阿贝里和布伦娜·泰勒被警方谋杀后,当下的政治能量将这个问题摆在了许多人的脑海中。
- 我们并没有要求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数学计算方式做出重大改变——许多人已经没有在专业工作中与警方合作,也没有计划在未来这样做。
当然,遭到军事反对高级数学家迅速行动,表达了他们对这封信的异议。几封写给反对该运动的编辑的信出现在AMS的通知当黑人和布朗人起来反对全国各地的警察暴力行为时,看到有这么多理由把人扔进笼子,虽然令人沮丧,但AMS决定为那些认为我们应该继续与警察合作的人提供这么多空间,这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博客上回复我们利用这一刻,对专业数学的实践提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废奴主义立场,并扩大了我们的会员人数,增加了我们的劳动力,提高了我们更深入、更丰富的组织工作的能力。
经验教训:阅读政治能量并利用正确的时机对有效组织至关重要。那些经验不足的人,比如数学界的人,往往只准备迈出一小步,因此他们最愿意参加那些几乎不需要改变日常习惯的活动。
超越保密和监控的数学
在我们的数学超越监狱和警察运动奠定了基础之后,我们准备进行一个更为苛刻的组织项目。与当地警察部门相比,安全和监视组织在我们的社区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归根结底,国家安全局(NSA)、中央情报局(CIA)及其国际类似机构都是警务组织。他们采取行动维护与当地警察部门相同的压迫等级制度,并将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异议视为犯罪。正如我们在竞选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世界上如此多的黑人、布朗人和土著人来说,成为国际数学界的一员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是这些组织所表现出的残忍。因此,我们认为,以公平、包容或社会公正为中心的数学活动,包括国家安全局或任何相关机构的招聘,本身就是失败的。培养新一代黑人、棕色人种和土著帝国主义者在社会上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围绕着要求有良知的数学家退出这些机构。我们设计了一个认捐活动这允许签署国挑选自己的承诺,从与同事分享文件和引发讨论,到拒绝与国家安全局合作组织会议和批准提案,再到拒绝为国家安全局相关项目撰写推荐信。这种灵活性允许人们只登录他们认为可以亲自支持的活动部分,我们注意到这鼓励了更多的参与。
我们对这场运动围绕这些问题所产生的能量感到激动,我们也感谢已经签约的数学家人数。尽管参与起来很容易,但仍有很多DEI专家他们肯定已经听说过这场运动好几次了(我们已经确定了!),但还没有参与。就这场运动而言,这些人离冷漠的学术而不是他们愿意承认的。
如果你是一位对DEI工作感兴趣的资深人士,并且你认为我们指的是你,那么我们可能是。我们希望您能参与我们的任何活动,并且我们始终留有增长的空间——即使您觉得现在无法支持这一倡议,我们也不会放弃您。但与此同时,我们鼓励您参与即使意见分歧你有自己的观点;推动你克服对公开发布它的恐惧,是激发行动、成长和对话的动力。简言之:用你的胸脯表达不同意,而不是沉默。
这里不是重提围绕这场运动出现的所有争论的地方:读者可以查看常见问题解答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然而,我们确实想强调一个典型的问题:
“我只是一个人,在一个基础研究资金越来越难获得的环境中,我正在努力获得资金。如果国家安全局无论如何都要发放资金,而我的工作实际上与国家安全没有什么关系,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们真的很同情这种观点!但我们也觉得,这误解了像国家安全局这样的机构对其赠款的影响。资助组织争取更大比例的总奖励资金,以便能够更积极地塑造研究格局。在一个监视机构负责大部分可用资金的世界里,也是一个这样的世界:
- 对a的研究数学为人民服务(例如,为人们开发开放源码和免费可用的技术,以保护自己免受警察和政府监视)获得资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此根本不太可能实施;
- 甚至是那些对一 数学为人民服务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追究监督机构的责任,而且他们有政治黑名单的历史。
再次,我们看到了个人主义框架是如何以林代树的。只有当我们缩小视野,思考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时,我们才能看到什么是“大事”,作为一个社区。只有通过集体努力,我们才能消除它对数学的束缚,因为这里需要做的改变有大的包括:向当权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努力游说,争取从监测机构中分离出更多的基础研究资金,以及集体思考更多合乎道德的工作机会这样就没有人必须在离开数学和与警察局合作之间做出选择。
除了要求数学家做出个人承诺外,这项运动还呼吁AMS解释其与NSA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不要向监测机构提供在联合数学会议上招募人员的空间和资源。活动参与者被要求向AMS发送电子邮件,AMS在其总裁的官方电子邮件中作出回应,声称“AMS邀请任何潜在的数学家雇主与我们的社区接触……”考虑到数学的实用性,以及许多拥有权力和金钱的组织,他们也是积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酷儿和跨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等,我们需要AMS来澄清其含义。
这场运动很活跃,未来的规划阶段我们还不能多说。目前,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接受承诺,并通过发送邮件加入电子邮件操作此更新的脚本响应AMS。我们还敦促所有声称关心正义的专业协会听从我们的呼吁,承诺不接受国家安全局和其他监督机构的任何资助。光谱这样做已经设定了标准-你的组织需要什么才能成为下一个?请加入我们!
经验教训:提出更大的要求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努力,以达到同样的参与水平。将灵活性融入到活动中可以让人们选择他们想要的参与方式。我们正在寻求的那种变革需要长期规划和无止境的竞选活动。当我们为数学正义而战时,我们不仅仅是为受压迫的人民而战。我们也在为我们自己的数学社区的健康和资金充足的未来而战。
抵制、撤资和制裁的数学家
在行动日(5月18日),为了声援巴勒斯坦起义,并鉴于以色列最近对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暴力升级JMC正式支持巴勒斯坦人呼吁学术界抵制以色列并敦促个别数学家及其社会效仿。虽然这场运动在废除死刑的目标方面与我们的前两次运动非常相似,但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它与之背道而驰,因为我们没有设计它的指导方针。我们争取解放巴勒斯坦的运动属于更广泛的范围巴勒斯坦领导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这是一个已经在积聚势头,同时也在忍受各种形式的镇压的国家。
诽谤者如何表达对任何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言论或行动的反对,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模式,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模式在我们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发挥了非常可预见的作用。我们不会在这里解决所有反对意见,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活动文档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正如在最后一节中一样,我们将重点介绍与这篇文章的共同主题有很大关系的一两个方面:权力建设是集体的,当我们为一个真正公正的事业挺身而出时,我们就为每个人挺身而出,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将花一些时间讨论的第一个常见反对意见围绕着学术自由:
“我不能参加,因为这次抵制是对以色列数学家学术自由的侵犯。”
我们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抵制的指导方针是明确的:个别学者不可容纳儿童。特别是,与以色列机构的数学家合作,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和研讨会,并在非以色列机构主办他们不构成对抵制的违反。“学术自由”的稻草人作为一个论点尤其荒谬反对抵制针对机构努力沉默、骚扰、恐吓和惩罚任何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人。更不用说,巴勒斯坦学者的学术自由或流动性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这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殖民范式是一致的。
通过支持以巴勒斯坦人为首的抵制呼吁,我们同时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自由,以确定自己抵抗的最佳战略,并尊重我们自己的表达激进政治信仰的自由。许多人因声援巴勒斯坦而被列入黑名单、解雇和回避(其中许多是黑人、棕色人种、阿拉伯人、穆斯林和/或犹太人),民权组织称之为言论自由的“巴勒斯坦例外”。这是这个当涉及到表达激进和公正政治观点的权利时,战场问题,所以当你加入我们时,你也在为自己而战。
我们将强调的第二个常见反对意见侧重于疗效和影响:
“学术抵制影响不大。我去Technion参加会议的决定与运动进程无关。”
从精神上讲,这一反应与我们在上一节中花时间讨论的反应几乎相同:我只是一个人,那有什么大不了的?集体权力建设的全部意义在于,当我们加入一个运动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再只是少数持原则立场的学者。我们是来自许多的工业-运输/进口/出口,艺术与文化,研究与开发农业、建筑业等等他们站在一起反对种族隔离和定居者殖民主义。除此之外,学者,尤其是数学科学家,在这里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学术界在塑造和改变文化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而占领和种族隔离政权严重依赖我们学习和教授的数学技术。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这场竞选比其他任何一场都更具挑战性。我们很高兴(到目前为止)找到65位数学家,他们已经准备好与我们签约,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理解,人们害怕宣称自己的权力。我们理解这一点,并对此深表同情,因为我们中许多已经签约的人也很害怕。但我们还是这么做了,因为有必要符合我们对上面关于权力一节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这就是我们如何使用权力做必须声援受压迫的人民。如果你持观望态度,并且你在这里读到的内容与你产生了共鸣,那么问问自己,你将如何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保持一致。请记住,当您加入我们时,您可以降低每个人参与的风险。
此活动处于活动状态,您可以通过登录加入在这里.
经验教训: 采取这种立场时,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恐惧。克服这种恐惧需要更有针对性的组织策略:一对一对话、政治教育和小组讨论。进展缓慢,但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和产生影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