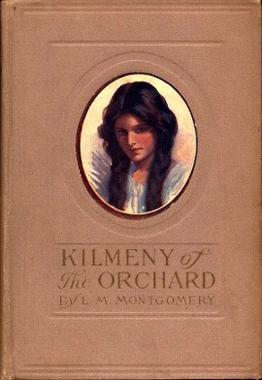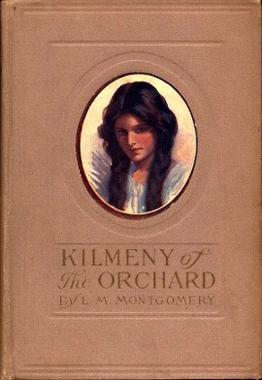我的甲状腺和我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很好——我过着自己的生活,它为我提供了所需的荷尔蒙。大约二十年前有一次事故,当时我突然注意到我的甲状腺肿块。它大约有四分之一大,里面装满了什么东西——感觉像是半个水气球。我去找了一位内分泌学家,他给了我一个关于甲状腺癌的长篇大论,我想,这对帮助他的住院医生来说,要比对我来说更重要。他把一根针插入水气球里,取一些液体进行测试,水气球就泄了气。检测结果呈阴性。它什么都没有——一个无害的囊肿。
因此,圣诞节后不久,当我再次感觉到甲状腺有肿块时,我有了一些背景。我大致知道它可能是什么。我设法在我的初级保健提供者工作的诊所预约了一个时间——等待了两周,我只能去看执业护士。显然,所有真正的医生都很忙。当我试着预约的时候,接待员也在忙着和她的朋友聊天。那是我预约之旅的开始,每个预约系统都和第一个一样糟糕。我有一个理论,在美国,医疗保健最困难的部分是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预约。当然,第二个最困难的部分是计费系统。我试着向欧洲朋友解释“共同付费”。他们茫然地盯着我。
执业护士安排了一系列测试,所有测试都恢复正常。她还要求做超声波检查,为此我不得不去波士顿医疗中心。超声结果出来了。我的甲状腺有一些结节。他们看起来很正常。不建议随访。但我的喉咙还是有肿块。我的母亲碰巧是一名医生,她说:“你需要对它进行活检。”所以我写信给执业护士,我需要对它做活检。她给我推荐了一位内分泌学家。我打电话预约了。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打电话预约。有一次,我在六个月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我被告知没有,那只是给回来检查的病人,有人会给我回电话;我被告知需要与艾希礼通话的电话;阿什利不在的地方;我被告知取消了上课,我明天可以来,我必须解释说我是一名教授,正在上课;与艾希礼的电话;与Ashley的后续电话。然后我有一个约会,从我和艾希礼谈话的一个月起。(你不能打电话给阿什利或其他任何人预约。你必须拨打中心号码,在录制的信息中单击所有正确的按钮,等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你从未听过的音乐,然后与告诉你其他人会给你回电话的人交谈。)
在我得到预约和预约之间,我喉咙上的肿块消失了。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这并不意味着根本没有问题。无论如何,我已经和内分泌学家约好了,所以我去了——只是为了确定肿块确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内分泌学家自己又做了一次超声波检查。显然,第一次读超声波的放射科医生计算错了结节的数量。事实上有四个以上,除了左边的两个外,大多数看起来都是无害的。“那里有很多血管,”她说,把一根冷棒放在我的喉咙上。我很幸运,我知道血管化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我有英国文学博士学位。这不是医学博士学位,但它是一个文字博士学位——它们的意思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博士学位,当我不明白什么的时候,就去查。在与美国医疗系统打交道的每一点上,我都想知道一个没有高级语言理解学位的人,一个甚至可能不会流利英语的人,会如何应对。“我们真的应该对那些特定的结节进行活检,”她说。于是她用一根细长的针做了。
较大结节的活检结果显示“怀疑恶性”。可疑,不确定。即使这是确定的,但这种活检(FNB或细针活检)的问题是,它从来没有真正确定过。FNB只能给你一个百分比的确定性。官方的“可疑”比例是恶性肿瘤的15-30%。事实上,这很可能不是恶性的。但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定。内分泌学家说:“我建议做手术。”。“我会让人给你打电话预约外科医生。”所以我又进入了预约系统,但这次是在内分泌科。这个系统的Ashley被称为Blaise。一旦你能与世界各地的阿什利和布莱斯人交谈,一切都会顺利进行。诀窍是识别他们是谁,然后找到他们。
这位外科医生和他的同事(甲状腺问题专家)再次进行了超声波检查。他们告诉我,除了那两个结节外,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我的淋巴结看起来很好。我的甲状腺另一侧看起来很好,那里的结节是无害的。但我的甲状腺有可疑结节的一侧,应该去掉。他们建议进行甲状腺叶切除术,即外科医生切除一半甲状腺。这是一个严重的手术,但成功率很高。即使患者患有甲状腺癌,长期生存率也为99%。我记得20年前第一集的一件事是,内分泌学家告诉我,告诉住院医生,如果你要得癌症,甲状腺癌是最好的癌症。
困难是,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发生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为15-30%,而非恶性肿瘤的几率为70-85%。这就是我所掌握的信息,我必须基于此做出决定。FNB并没有给你确定的答案——它只是通过针头拔出的一小部分细胞。唯一确定的是手术后,当他们对整个结节进行全面、真实、正式的活检时。那么你肯定知道了。但到那时,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又和内分泌学家谈了。她说我可以选择手术,也可以推迟到秋天再做决定。我们可以再做一次FNB,尽管它不一定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问她。“手术,”她回答道。我又和外科医生谈过了。在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我几乎笑了好几次。这几乎就像在医学院上课一样。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母亲是医生,而我是大学教授,所以他把一切都解释得很透彻,充满了复杂的不确定性。我再次想知道,如果我不理解拉丁裔术语,我在美国医疗系统的经历会是什么样子。但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大词并不能帮助你做出决定。“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在电话里问他。“手术,”他回答道。
最后,我基于两件事做出决定。第一个是外科医生说的。他说:“如果你的甲状腺那边的一切都很清楚,很容易观察,我就可以等着再做一次超声波检查。我们可以看到结节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是你的甲状腺那一边看起来很奇怪。”“奇怪”这个词打动了我。你真的不想让内分泌外科医生说你的甲状腺看起来很奇怪。另一件事是我在这个身体里住了很长时间。我相信它。我知道它什么时候想要告诉我什么。首先,它让我大吃一惊。直到我预约了内分泌医生,肿块才消失。我想我的身体是想引起我的注意。从那以后,我一直能感觉到,我的喉咙的那一边有点不对劲。我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感觉到一种压力。它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还让我轻微咳嗽。当我告诉外科医生这件事时,他怀疑地看着我。“也许你能感觉到喉咙里的结节,”他说。“你的喉咙很细,所以你可能能感觉到。”根据我的经验,医生从不相信你了解自己的身体。他们很确定自己比你更了解——毕竟,这是医学院教给他们的。他们是人体专家。但我在身体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知道什么时候不对劲。
就这样。星期四我要做手术。从理论上讲,我左边的甲状腺应该接管整个甲状腺的功能。希望我不需要药物,但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喉咙上会有疤痕。我打算告诉大家,这是我当海盗女王时的事。或者是我在法国决斗,但你应该看看我对伯爵夫人做了什么。或者我通常会戴天鹅绒丝带,小心,因为我的头可能会掉下来。
更平淡的是,我会尽我所能完成期末评分。然后是布达佩斯,然后是伦敦,然后是我的余生。半个甲状腺总比没有好,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进行更多的冒险。

(图像是女人在床上读书作者:Gabriel Ferrier。这就是我手术后一周内的计划。)